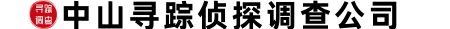侦探案例
咨询热线
13728687007电话:13728687007
传真:13728687007
邮箱:admin@youweb.com
中山哪里有可靠私人调查公司-从《图腾制度》到《菊与刀》: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扬·普兰佩尔,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专注于情感史与感官史的研究。在其著作《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中,他详细回顾了从启蒙时代至大众传媒时代的情感发展轨迹。这一过程涵盖了从拿破仑致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致女儿们的家书,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以及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等作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情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催化角色,而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手法亦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本篇内容节选自《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这一章节,由澎湃新闻在世纪文景的授权下进行发布。
涂尔干虽曾研究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未曾亲自踏足长途旅行。他的学术研究是基于既有的人类学成果。他着重关注的是:是什么力量将社会紧密团结;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集体表征”问题,这其中包括仪式及其作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对情感与情感表达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12年,他在文中如此记录:
哀悼并非单纯由个人情感自发产生。家属们哭泣、哀痛、折磨自己,并非因为他们本人真正体验到了逝去亲人的影响。当然中山专业调查公司哪家好,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人们或许能真切地体会到他们所表达的哀伤。然而,通常情况下,他们所体验的情感与在仪式中采取的各种行为并无直接关联。当人们沉浸在悲痛的泪水中时,若有人提及一些与世无争的话题,他们往往会迅速转变表情和语气,开始轻松谈笑,这情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故而,哀悼并非仅因亲人离世而自发流露的私人情感,而是社会强加于他们的义务。一个人之所以落泪,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感到悲伤,而是因为他被迫如此。出于对传统习俗的敬重,他不得不接受这种仪式上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未与他内心的情感产生共鸣。此外,这种责任还受到神话及社会惩罚的明确界定。比如,他们坚信,若有人在悼念逝者时未能表现出恰当的哀悼之情,亡者的灵魂便会紧随其后,直至将其夺去生命。
若将时间线向前推进,我们便会发现,欧文·戈夫曼(1922—1982)对于社会面具与所谓“真实面容”或个性的明确划分,不仅彰显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时也映射出涂尔干对仪式的深刻见解。更进一步,若非涂尔干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对情感仪式化的独到阐释,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当代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将何去何从。
现在,让我们重返涂尔干及其对宗教的探究。在他看来情感与形式,宗教远非仅是功能性的存在,亦非社会成员在遵循推动社群进步的既定社会规范时的行为模式。宗教更涵盖了宗教仪式与集体情感激荡的“沸腾”状态。在此,我们不难察觉古斯塔夫·勒庞思想的痕迹。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至2009年间,无疑是20世纪法国人类学的巅峰人物。他与马塞尔·莫斯同出一辙,均深受涂尔干学说及德国学术传统的熏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41年至1948年美国逗留期间,弗朗茨·博厄斯对他的影响亦不容小觑。此外,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纽约期间,他与罗曼·雅各布森展开了紧密的合作。那时,他还深入研读了结构主义奠基人索绪尔的著作。
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重返法国,着手对图腾制度进行探究,并随后转向宗教与情感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众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曾基于“原始”民族与图腾(通常源自动物符号)之间的关联,构建了各自的宗教理论。例如,涂尔干提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揭示了宗教生活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图腾的运用并非标志着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倒是展现了某种极具成效的认知训练方式;在这种情境下,抽象思维较为罕见。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众多研究图腾的知名学者,如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克罗伯,他们都将图腾的起源归因于情感,即认知的相反面,因此,他们放弃了提出科学解释的尝试。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感性作为人类最难捉摸的特质,因此常常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情感寄托,然而,许多原本并不适合用感性来解释的事物,也就随之被遗忘了。
涂尔干提出,人类通过情感因素塑造动物图腾,其目的在于与已故的先祖们建立某种联系。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他反驳了所谓的“神圣情感理论”。
实际上,冲动与情绪并不能提供任何解释:它们通常只是结果,可能是体力消耗后的产物;也可能是精神能量释放的后果。在这两种情形中,它们都只是后续的效应,而非最初的动因。
在情感领域,列维-斯特劳斯被证实是众多实验心理学家中的一位唯物主义者,卡尔·朗格(1834—1900)与威廉·詹姆斯受其思想启发,提出了极具潜力的理论。他们主张情感并非源自身体内部,而是肢体动作本身即情感的表现。后续的社会建构主义文献对《图腾制度》一书中涉及冲动与情感的篇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斯特劳斯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有相似之处,他在某种程度上为评价或意图论提供了思考的余地。有人觉得,他明显地将情感简化成了身体动作,这一行为足以使他成为心理学家西尔万·S.汤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1911—1991)的追随者。汤姆金斯是众多社会建构主义者所不喜的,同时也是保·埃克曼的精神导师。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民众首先领略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深刻影响,其中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追溯至1914—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的实地考察,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学科强调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以及原住民语言的习得。马林诺夫斯基明确指出,他的研究焦点在于亲属纽带,然而,他的个人日记却生动地揭示了人类学家在进行实地考察时所体验的情感。即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他同样感受到了这种情绪。
我对热带气候深感畏惧;对酷热和潮湿感到极度不适——一想到去年6月和7月那般的高温,便不禁心生恐慌……心情异常低落,担心自己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1914年9月12日(星期六),我抵达了新几内亚……我感到疲惫不堪,内心空虚,以至于我对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模糊不清……到了10月31日……由于当时那里并无舞蹈或集会,我便沿着沙滩漫步,直至抵达奥罗柏(Oroobo)。这是一次非凡的旅行经历。这是我首次在月光的映照下观赏这片土地的植被。那份奇妙与异国情调令人陶醉。这种异国情调悄然揭开了熟悉事物的面纱……引领我踏入丛林深处。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惧,不得不努力平复心情,试图审视内心:“我的内在生活究竟是什么?”我毫无理由地感到满足。
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被视为情感人类学领域的重要奠基之作。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情感是搜集资料的根本。于是,在接触观察对象的过程中,情感交流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被观察者的情感往往与观察者的情感产生互动。
威廉·哈尔斯·里弗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又一重要开拓者,生于1864年情感与形式,逝于1922年。在他作为人类学家的生涯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他始终致力于学术研究,足迹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战争岁月里,他对医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投身于精神病医生的职业,专门为那些饱受“炮弹休克”之苦的战士提供医疗服务。他的英勇事迹,得益于派特·巴克所著的《重生三部曲》(1991—1995),如今已被世人传颂。里弗斯与西格夫里·萨松,以及苏格兰克雷格洛克哈特精神病院的其他患者之间的书信往来,已成为一战的宝贵文献之一。至于他的创伤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实地考察的启发,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里弗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在1922年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情感”是一种围绕特定对象构建的有条理的情绪倾向体系。他认为中山专业婚外情调查公司,一个社会的持续存在依赖于其成员内心是否拥有某种特定的情感体系,该体系能够调节个人的行为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情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个人在社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在1931至1937年间在美国担任教职,因此深受涂尔干学说的影响。因此,德国的人类学虽处于相对的低调状态,然而,巴斯蒂安借助博厄斯、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涂尔干的影响力,对美国的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借助巴斯蒂安的“儿子”弗朗茨·博厄斯,我们可以追溯至他的“孙女”鲁思·本尼迪克特,她于1887年至1948年间生活,并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际迅速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菊与刀》,该著作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学特征。本尼迪克特不仅使人们广泛认识到日本“羞耻文化”与美国“内疚文化”的差异,而且她深入研究了引导日本社会生活的情感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与北美的相似观念进行了对比。比如,在日语中,“恩”这一概念贯穿始终。它融合了“爱”与“尊重”,同时亦代表着责任以及对某人的感激之情。我们高度重视爱、关怀、慷慨和仁慈等价值观,其中,无条件的爱尤为珍贵。然而,在日本,这些情感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条件。在《人情的世界》这一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详细阐述了日本人对于五种情感的认知及其相应的行为准则。
玛格丽特·米德,生于1901年,逝于1978年,曾是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她可以被视为巴斯蒂安家族的“后人”。米德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史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贡献之大,任何赞誉都显得不足为过。在1925至1926年间,她对萨摩亚群岛的实地考察充满了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这一观点后来对美国教育的变革以及种族关系的重塑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她对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女性)的刻画,也为性革命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观察到,波利尼西亚人……
对情感表达的态度与对行为举止的看法一样,显得格外独特。在情感表达的众多方式中,它们被划分为“情有可原”与“毫无缘由”两大类。那些情绪波动大、喜怒不定的个体,常被指责为无缘无故地欢笑、哭泣、发泄怒火或表现出好斗性。“无端暴怒”这个词语并不等同于脾气暴躁,脾气暴躁通常用“易怒”来形容;它也不代表对恰当的刺激有过度的反应;实际上,它只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即毫无缘由地感到愤怒;用不那么严谨的说法,就是指那种并非由任何明显刺激引起的情感状态。
总体而言,米德提出萨摩亚人倾向于走一条中庸之道,即情感表达上的适度。相较于其他人类学家,米德的研究更为清晰,他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向美国社会展示了一面反映自身文化的镜子。她强调,在美国的核心家庭模式中,追求情感的专门化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这是因为一个由几位成年男女组成的较大规模的家庭群体,似乎能够确保孩子们不会形成某些缺陷性的心理态度,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等。
随后,众多人类学者纷纷效仿米德的研究路径,正因如此,众多关于情感的学术探讨均以研究南太平洋诸岛为基石,而非立足于非洲、南美洲或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之上。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情感与形式,美国人类学界崭露头角一个崭新的解释学分支,这一流派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以及克利福德·格尔茨夫妇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仅能找到克利福德·格尔茨对情感的一些论述,例如“文化不仅塑造了思想,同样也塑造了情感”,还有“若要作出决定,我们需了解自己对事物的感受;而要了解自己的感受,我们便需要感情的公开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唯有通过仪式、神话和艺术才能实现”。在研究情感表达仪式的特征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研究成果常被引用。他的首任妻子希尔德雷德更看重情感层面。她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类普遍有表达共通情感的倾向,然而这一倾向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因文化因素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这些文化因素带来了多样的影响,导致情感特征各异。有的文化推崇特定的情感表达,而另一些文化则倾向于抑制这些情感。希尔德雷德·格尔茨在探讨爪哇人时,倾向于采用一种现下看似陈旧的普遍视角,即便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研究相比亦然。她指出,爪哇人并不倾向于激烈的情感流露,他们鲜有深厚的友情或爱情联系。爪哇的女性,相较于男性,显得不那么安静和顺从,她们在情感表达上更为主动。此外,她还提到,恋母情结的矛盾在成长过程中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尽管存在这样的背景,她仍旧对当地居民的情感观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这些观念无不与敬意紧密相连,并在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中被传授。基于此,她总结道:“儿童教育体系”不仅是情感社会化的核心要素,亦是社会对个体内心情感世界所持信念的核心要素。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由扬·普兰佩尔撰写,马百亮与夏凡共同翻译,由世纪文景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7月出版发行。